
有一个让我们心碎的问题,就是,这一生,无论你过得得意还是落魄,最后,都要死去。或者,您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作者,我,已经死了,化为尘土,了无痕迹;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很多读者,也都死了,刹那刹那;还有,当您放下这本书的时候,您身边的人也有很多在死亡;在一段时间之后,您自己,也会死掉;还有的人从未读到这本书,当然,更不知道我们用文字这样交流死亡,他就两腿一蹬,死了;还有人,从没有认真思考死亡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忽然死了;还有人竭力不让自己去想,如鸵鸟逃避危险那样,把脑袋扎在沙子里,把屁股撅在外边;甚至,还有人,还没从子宫里出来,就被大夫的产钳不小心给活活夹死了。
这一生,最长不过百年。短不过几十年。
而已。
人类,乐观的时候挺可爱的,但有时候也不可理喻,很荒唐,明明就活这么些年,却偏偏都给自己规划出丰富而长远的人生计划,仿佛都能活几百年乃至千年。
千秋万代。
这个汉语成语是用于我们表达对政治、财富的美好以及贪婪的期待。
我们已知的、公认的、并且有确凿物质证明的人类历史不过几千年。辉煌而鼎盛的朝代也不过几百年。
对我们的物质身体和我们几十年的寿命而言,放在人类思想根本无法想象的漫长宇宙和时间长河当中,算什么呢?
任何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死亡来说,都如此的脆弱。令我们伤心不已。
我们有能力探索死亡的秘密吗?甚至,我们能够驾驭死亡吗?
我父亲曾经判断他能活八十多岁,他的理由是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活到八十四岁。他说,他老人家清末时出生在大山沟里,经历了诸多战争和诸多灾难,生活的时代条件那么差,都能活到八十多岁,按照时代进步发展的规律,他自己怎么也不会比他的父亲寿命短吧。
我父亲对自己的长寿还有一个重大物质信心,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他也期待自己的长寿能够让自己更多地享受儿孙绕膝的美好生活。
遗憾的是,他老人家七十三岁那年死了。
我父亲有多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他患有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病的学名是一个我一辈子都记不住的外国名字。父亲在中年时曾为此在上海做过一次很大的手术,这次手术的风险很大,死亡概率很高。
麻醉期间,父亲说他有意识。
他说他要去一个地方,被别人拒绝,然后就醒来。手术已经结束。父亲说那个“梦”很让自己恐惧。
手术成功之后的多年,父亲患了多种疾病,又经过了一些小手术,包括一次阑尾手术。后来是严重的肺病。父亲的后半生就这样不断地跟疾病做斗争。记忆里,我和我的哥哥们一直陪着他在各个医院的挂号处、手术室、病房里斗争。
后来,我把父母从安徽接到天津,我们过了一段为提高生命质量而经历的最朴素和低级的生活方式。我购买了一个父亲很喜欢的房子,每天给他买牛奶喝。幸亏他老人家不太爱喝牛奶,否则后来他死的时候肚子里还得有结石。
金钱并不能给父亲带来快乐。即便有快乐,但是,这快乐很快也要因为死亡的到来而成为巨大的悲伤,要知道父亲是多么喜欢我和我的两个孩子啊。况且,死亡到来之前还有疾病的痛苦,没去过医院的人真应该多去看看,人生在世,什么样的疾病都有,什么样的痛苦都有。我父亲还得过一个病,本来是治疗肺的,肺没治好,忽然尿不出来了。这时候才知道,活人是可以让尿给憋死的。没办法,就在尿道里插一根管子,外边接一个塑料袋。塑料袋不能挂在外边啊,就揣在裤兜里。膀胱里有尿了就流到袋子里。
后来,治好了前列腺,父亲的下巴又掉了,而且总掉。再后来,七窍流血。一流就是一脸盆。继续不停地去医院和疾病做斗争。直到有一个早晨,他忽然拉着我不让我上班,说刚刚自己做了一个“梦”,但又确定不是 “梦”,他在黑暗中行走,看到了很多人,包括过去已经辞世的人,其中很多是被他帮助过的人,几十年前,旱灾时,父亲的钻机在很难打出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些人,他都一一看到了。
因为恐惧,父亲从黑暗中逃了出来。就“醒”了。父亲一脸的惊恐。我从未见到一生坚强的我的父亲如此地恐惧,恐惧到拉着我的手死活也放,不让我离开他,不让我出门。他面部扭曲,泪流满面。
那时候,我已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父亲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我们开始谈论死亡。
我认为,人活着就一定要为死亡做准备,而不是莫名其妙地活,莫名其妙地死,只是简单地追求物质享受,那就更没劲了。
我决定,不能让父亲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掉。
我看过一些书,给父母念经咒会对他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利益。去寺院里皈依更有好处。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地,但,我想,总是有利益,为什么不做呢?
父亲在天津的挂甲禅寺参加了一场很庄严的皈依仪式。
回来后,我们继续谈论死亡。我告诉父亲,一定要对死亡有所准备。但父亲却拒绝谈论这个话题。对我的人生观不置可否。
我给他念经咒,他倒是听。只是有时候觉得太长了,希望我要是再念能不能念短一点的。
我想,他依然没有面对死亡的想法和勇气。他愿意听经咒,是因为喜欢和我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我们之间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暴露了。
那是一个清晨,我给父亲念《佛说阿弥陀经》,经本是繁体字的,手写的印刷的那种,我记得很清楚,听别的经父亲都打瞌睡,或者听不懂,但《佛说阿弥陀经》他听懂了。在窗边,在充足的阳光下,父亲主动把经本拿到自己的眼前,读上面的文字。
读到“极乐世界”,父亲说,哪里有“极乐世界”啊,没有的。
我说,有,我的父亲。
父亲沉默了。
我知道,我和我父亲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沟豁。很难逾越。
父亲要一个物质的证明,证明极乐世界存在。而我却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智慧去证明极乐世界的存在。
但,父亲的死亡是无法逃避的。
我找到了一些光盘。感谢生活,我没有能力和智慧,但世界上存在着那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一张“赵荣芳老居士往生”纪实的光盘完整记载了一个老人在临终前几年一心念佛,最终往生西方的过程,火化时,老人的骨灰里有舍利,最不可思议的是未燃尽的一根骨头上竟然清晰地附着着佛像。
还有一张盘,记录的是有一名居士竟然站在那里往生了。遗容微笑祥和,尸体数日柔软。
还有几张台湾的居士讲述死亡和往生的事情的。包括很多高僧大德讲法的光盘。
在家闲着没事的父亲看了这些光盘,其中,看到一个台湾居士讲述他父亲死亡和往生的光盘时,忽然潸然泪下。
也许,那张盘让父亲接受了死亡的现实。
我父亲小时候受过简单的教育,1949年以后在地矿部接受过文化教育,搞了一辈子地质钻探,文化水平不高。如果他活着,我想,上面的这些文字他很难深入阅读。
依我当时对佛法的认知,就是让他老人家念佛。
虽然我也是人云亦云,但是,依然还是那个大道至简的道理,跟深信因果和众善奉行、诸恶莫做一样。简单的可能就是最行之有效的。
很多大师也都这样讲。
我相信大师们的苦心,相信高僧大德们的智慧和证悟。一定错不了。
在龙泉寺,一名在我看来修为很高的僧侣,就这样嘱咐我们,要多念佛。当然,他也带领我们阅读经藏,也常谈“空性”,也有类似禅宗的机锋交流。
但他说,他修习过多个法门,都有心得,绕了一圈,最终要“导归极乐”,还是要多念佛。以念佛的功夫开智慧,以念佛的功夫往生。
当然,我觉得他这话是对我这样根器差的人说的,对那些智慧高的,根器深的可能会有更高的法门。经上说有八万四千法门,但我觉得在山上听到的这些已经很受用、很受用。
当然,您读到这里,会顿生疑惑,持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死亡问题吗?
这和极乐世界的问题一样,是一个很深的沟豁,很难逾越。我们熟悉的六道轮回也是如此,很难逾越。信与不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法华经》中讲,轮回中做人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按照现在人们的起心动念和行事看,去恶道的做畜生和饿鬼乃至地狱的居多。
信还是不信?这已不是文字所能够表达的。
信什么不信什么,不是光靠文字来的,要靠感觉的。我听一个僧侣说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出家前,他是个天才少年,刚出家的时候,内心很傲慢,谁都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很有修为的师兄叫他,来。
他傲慢地说,干吗?
这位师兄说,不干吗,你在我身边坐一会儿。
他说,坐就坐,有什么了不起。
于是,两个人安静而无言地坐着。
之后,他彻底心悦诚服,安心修道,降伏住内心的傲慢。
这个感觉也让我很信服。我也不是靠一两张光盘,读一两本书就能对他们服气的人,但是,当你在那些真有修为的人身边一待,你所感知的力量,慈祥,你所觉受的气息足以让你对人生进行重新地审视和觉察。
我有幸和龙泉寺的方丈(注:学诚法师)有过几句话的交流,也在他老人家身边磨蹭过,所感受和觉察的善的、智慧的、觉悟的气息,绝非语言可以表达。
我父亲没有我的这么幸运,他没有机会和大师交流,所以就半信半疑地,偶尔为了敷衍我念几句佛,大多数时间就傻待着,闲着睡觉,看电视,以及和疾病做斗争。直到有一次,他必须做一个彻底的抉择。
他老人家得了严重的静脉曲张,一条腿已经黑了。
而且整个人已经萎缩,脸上和身上的皮肤全都皱得如老树皮一样。去医院看病,大夫说,这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外有个零件坏损,可以通过手术解决,但是,父亲的身体条件是绝对经不起这个手术的。
去看中医,中医大夫很有道德感,说,可以治好你的病,但是,下药后会对你的肝脏有严重的损伤。
这病就等于是没治了。
静脉曲张不能治疗的最后结果就是腿部坏死。最后截肢。
父亲再次极其恐惧。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的老同事截肢的痛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单位里有个同事脑子很好使,往上爬的本事大。老实的就只能埋头干活。此人年轻时很风光,老了很惨,先是左胳膊坏了,截肢,右胳膊坏了,又截肢,一条腿又坏了,截肢,另一条腿也坏了,又截肢,最后就剩个脑袋和身子在床上躺着。痛苦之极。
我跟父亲说,这好象不是我们能解释得了的,也不是一个偶然。肯定是有规律的。您年轻时没做过什么坏事,老实工作了一辈子,还救了很多人,一定会有好报的。现在中医也不能治了,西医也不能治了,我是您的儿子,您应该信任我,咱们念佛吧。信不信也就这一条路了,没别的路了。
父亲开始念佛。
数月后,父亲的腿开始逐渐好转,最后,一条腿竟然完全好转,只是脚面上还残留几点静脉曲张的黑青色的淤色。
父亲脸上的皱纹开始减少,面色开始红润。手上的老树皮一样的皱褶也消退。当年,他的手竟然和我的手差不多了。光滑而干净。
老人家高兴坏了,再不用担心截肢了。
我们继续谈论死亡,为死亡做准备。
没多久,父亲又因心脏的问题病了,再进医院,这一次,又有濒死的体会。他说,在医院里,大白天,他正躺在病床上做“梦”,忽然有两个人进来,到病床边,要带走他。
惊恐中,父亲醒了。
这次,出院后,我们对死亡的认知越来越现实和清晰。
每周末,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一定陪着父母,躺在父亲的腿上,和他说话,谈过去的事情,谈念佛,谈死亡。
有一次,父亲惊讶地说,我相信念佛了,因为,我念的时候,后面有人跟着我念,回头看,什么也看不到。
遗憾的是,我没有一直陪着父亲。因为家庭矛盾,父亲要回安徽,和二哥一起生活。
回安徽的第二十八天,他去世了。
这期间,他看望了所有能看望得到的老领导,老同事。我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发现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银行的密码以及种种可能给后人带来麻烦的事情都做了详细地交代。
去世的当天,他和母亲外出买早点,买完了,忽然在路边要坐一会儿,坐下后,往后一仰,母亲没有扶住。
事后母亲说,他当时就走了。
我二哥赶到时,先将他送进医院,抢救一番无效,给我打电话。我说一定要送回家,给他念佛。
按照佛教对生死的认知和告诫,人死后,不要动他,神识会有一段叫中阴身的阶段,他的意识和情感俱在,只是我们感知不到他的物理存在,但他能感知到我们。
这段时间,最好就是给他念佛号,让他有机会往生西方。
我二哥把他带回家。第十三个小时,我开车赶到安徽。哥哥嫂子一直在给他念佛。
当天晚上,我给父亲的遗体念经念佛,观察了父亲的神态,比较安详。请来的给父亲穿寿衣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感慨,说,这个老人很干净,这一行做了这么久,见过死人无数,包括我父亲在内一共经手过两个念佛的人,和别的死人确实不一样。
第二天一早,父亲门外的一棵盆栽的腊梅花忽然逆季节开放。
我没有功夫,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但,肯定不是不好的地方。虽然,生前,我们有过约定,希望父亲能够托梦给我,告诉我他去了哪里。
应该是我没有修为的原因,一直没有真切地“梦”到父亲。
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并不是离我们遥不可及,而是就在眼前。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在我的记忆里,很多艺术水平很高的文艺作品都是主人翁在遇到痛苦和困惑的时候跑到雨地里对着天猛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Why……Why……”作为高潮。
我们感动和被震撼之后,也不禁跟着为什么为什么……Why……Why……
喊两嗓子,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是令观者掬一捧热泪。
我老妈亲眼目睹了父亲经历的一切,身历了从贫穷到物质充裕但都没有获得快乐的全部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很神奇,也会觉得很自然,会有信心。有一段时间还抄写经文,也与我一起在寺院里做了皈依。她还回忆起很多过去自己亲眼目睹亡灵的事情。
但很奇怪的是,大多数时候还是稀里糊涂地,让她念佛,为了敷衍我,就说念了念了。
打电话问候她的时候,她听说我和孩子在寺院里学习,她会说,孩子为什么不去上学,哎呀,完了,完了,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赚钱。
我说,孩子在寺院里一样学习,而且还超级聪慧,我不做生意写字一样赚钱。
她老人家就开始狡辩,说,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要是谈起死亡的问题。她会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死了就死了。
我说,难道不想想死后的去处吗?可不能去恶道啊,到时候儿子上哪里去找您啊,我的亲妈啊。
我的可爱的亲娘铁嘴钢牙地跳着脚地说,不想,不想,就是不想。
对于人生的痛苦和出路的问题,山上的方丈学诚法师曾经在网上给我回复:“……平时多闻思佛法……世间的过患等,要认识到只有学佛才能使众生真正离苦得乐。”





















 大安法师
大安法师 如瑞法师
如瑞法师 慧律法师
慧律法师 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 省庵大师
省庵大师 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妙莲老和尚
妙莲老和尚 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 莲池大师
莲池大师 其他法师
其他法师 憨山大师
憨山大师 广钦老和尚
广钦老和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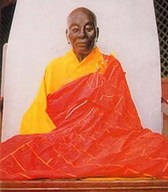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 净慧法师
净慧法师